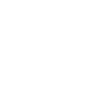青藏高原又称“世界屋脊”,是我国三大江河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长江黄河这两条“母亲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建设的全局。为了保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国家筹备在地处青海省境内的青藏高原部分建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2001年7月13日,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杨忠岐副所长带领的三江源科考队一行开始对长江、黄河、澜沧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考察队根据三江源的实际分为三组进行工作。考察期间科考队员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对三江源地区性区的生态类型、地貌特征、水文、湿地、冰川及分布作了实地考察,并对河流水文特征,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及保护对策、生态环境恶化的成因及治理对策等进行了多学科的全面调查,揭开了三江源地区的神秘面纱,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收集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黄河源头寻梦人 作为林业战线的一名工作者来,去黄河源头进行考察是一种常怀的梦想。 对于森环所杨忠岐博士来说,去黄河源头寻梦之路,却被危及生命的严重高原反应和冠心病所阻挡。7月15日刚刚带领考察队黄河组的同志离开西宁,到了海拔3800 米的温泉时,他便有了显的高原反应:头痛、呼吸困难。队员们纷纷劝他返回西宁以防不测,他却婉言谢绝了同志们的劝说,坚持与大家一同直奔黄河源头海拔最高的扎陵湖-鄂陵湖地区考察。但到了果洛自治州的玛多后,杨所长再也坚持不住了,强烈的高原反应使这位曾在科研路上从不屈服的科学家无可奈何地倒下了。玛多虽然是个县城所在地,但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一个小村庄,海拔达4300米,还没电,加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地磁小环境,人称青藏高原上的“鬼门关”。整个夜里杨所长昏迷了好几次,随行的大夫及队员心都要缩成团,靠吃了7次速效救心丸才熬到天亮,才被扶上紧急返回西宁的车。但到了西宁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他严重的高原反应还没有丝亳减轻的迹象,反而愈来愈重,这时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高原。现在他虽恢复了健康,但他一想到夙愿未了,总是嗟叹不止,这是壮志未酬的英雄之叹。 就在杨所长高原反应非常严重的那个晚上,其他的队员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高原反应。情报所的李忠魁博士夜不能眠、头疼欲裂,脉搏跳动达每分钟130次,就连素来对健康很自信的魏建荣也出现了恶心、头疼,周立志博士和黄桂林高工都食不甘味。可这些高原反应不过是这片神秘的土地给这些探险者们的第一道警告。当考察车行进在只有仅3米宽的倾斜山路上时,魏建荣、李忠魁与司机开起了关于生与死的玩笑。生与死这个永恒的主题,在那个辽阔、寂静的高原上被人们用一种调侃的语调来谈论时,却另有一翻滋味在心头。他们实实在在面对那瞬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能会发生的一切!当我们见到魏建荣和李忠魁并与他们谈论起曾有的险境时,他们只是说:“能去高原参加科考,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比起索南达杰我们不算什么。”索南达杰是一位为保护藏羚羊而献身的烈士。但我们心里知道,在保护人类家园的天平上,他们是同样的无价。 长江源头化艰险 在长江流域长大的李迪强博士则对长江更是怀有独特的情愫,去长江源头则是他久怀的梦想。但当他们离开西宁向长江源头进发时,他才意识到这种实现梦想的过程是那样的艰难。 对李迪强来说,那些装在尼龙袋中半生不熟的羊肉对他来说已不是一种享受简直就是一种煎熬。但为了增强体质完成任务,他还是强迫自己用藏刀割下一块又一块难以下咽的羊肉,塞进嘴里强咽下去。虽然这样,但这种毫无食趣而言的进餐程序已使他与这块神秘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苏化龙也能上高原?许多人惊异地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曾做过心脏手术,有这样病史的人上高原是十分危险的。但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毅然背起他所喜爱的摄影器材,与大家一齐跋山涉水,就在为拍摄难以爬上去的位于峭壁上的雪豹洞的时候他几乎从山顶上滚下来,但他的第一反应是象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紧紧地抱着他的摄像机。 杨正礼博士曾援藏6个年头,先后9次踏上青藏高原,高原反应是他的“老朋友”。但这次科考初期大家便连续在4600米以上的长江源头区工作和食宿,反应也很大。他一方面调整身体,深入社会、野外调查,一方面帮助大家消除恐惧情绪,克服困难,并与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当我们有机会见到他时,他却淡淡地说:“最伟大的是在高原上工作和生活的干部及群众,还有在考察中比我们更艰苦的后勤人员和武警战士,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无法完成这次科考任务”。 “爆胎”这个词若置于词典中会有轮胎爆炸之类的解释,但这个内涵简单的词在考察路上不但被高频地使用着,同时又被以“14”这个数字加以量化。而这种量化的背后则有摄影机摄不到、我们的笔无法触及的辛苦和劳累。 澜沧江头宿荒野 作为亚洲重要的国际河流的澜沧江,2号站对它的保护则不仅具有生态、经济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国际政治意义。 在澜沧江源头考察小组中,61岁的组长李建文研究员是被医生禁上高原的,但由于他的一再恳求,医生再也无法拒绝他的执着。在考察路上,他对各位队员的工作进行细致的安排,而且还悉心照顾着他们的生活,他的以身作则使队员们深受鼓舞和教育。 在考察途中,越野车一次又一次地陷于沼泽中,李老师也同他们的队友马强、韩景军一齐卷起裤管踏进沼泽。和其他组的队员一样,他们常住扎在破庙中,荒野里,对于爱幻想的人来说,这种生活该很浪漫,但对于身负重任的考察队员而言,这种席地而眠,露宿荒野的艰苦生活早已没了诗意。 在考察途中,年轻的队员韩景军患上了“带状疱疹”,2号站平台官网这种病俗称“缠腰带”,发作时疼痛难忍。本该返回治疗的他为了不影响考察工作的进程。依然坚持与大家一同完成考察任务。有时他们小组宿营在四处漏雨的废弃寺庙中,尚有水食,但有时汽车抛锚于荒山野岭,治疗就十分不便,但他硬是强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坚持了下来。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考查队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很多。 转眼已是初秋,科考队员们结束考察亦近半月。现在,他们正紧张地进行标本鉴定、资料整理、数据计算等内业工作。在他们考察的一个月里,不但对原定的核心保护区而且对缓冲区内的植被、野生动物、社会经济,人口、交通、工矿业生产、畜牧业发展、民族民风、水旱灾等进行了调查,并与当地政府、群众就保护森林、湿地、水源、野生动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许多宝贵建议。 在这不寻常的一个月里,他们的足迹到达了一系列生命禁区的山脉:阿尼玛卿山、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和可可西里山,行程一万五千多公里,2号站注册考察地区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胜利而圆满地完成了既定的考察任务。